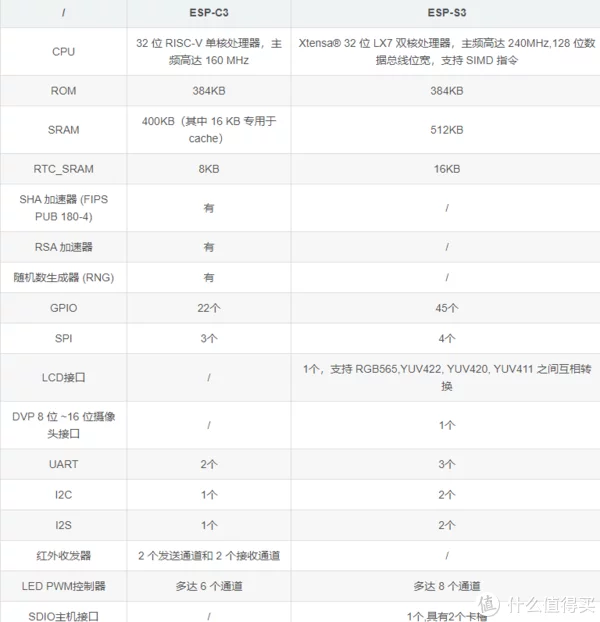作者:海边的西塞罗
卯字到底是什么意思?它的“黑历史”你不知道。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中国人一提起生肖属相,往往能讲的头头是道,你看网上现在一堆一堆说兔子咋样的文章。但对于属相前的那个“子丑寅卯”,多数人却说不出个子丑寅卯来。今天我就来聊个冷门,尝试为您解码一下卯这个字眼背后的密辛。
是的,你有没有发现,“卯”这个字在现代汉语中,有限的几个与卯相关的词,都是从“子丑寅卯”这一个意思中引申出来的。比如我们有时也把上班叫做“点卯”,这最初就来源于古代衙门要在卯时(早晨5点到7点)清点一下人数。在代表一种干支之外,“卯”似乎在现代汉语中就没有了别的意思,成为了完全用不上的一个死文字,很多人对这个字的发音甚至都要纠正——它读mao,三声。
然而,如果你去看汉字的最初缘起——商代的甲骨文,你会发信“卯”这个字相当之常用,高频到与北京人一见面互相问候“吃了么您内?”一样频繁。

这时因为“卯”在当时可不是个只标度干支的符号,它是有一个商代人常用的具体意思的——指将祭祀用的牲畜或人(尤其是人)剖开(尤其是从背部剖开),由于失去了胸骨或脊椎的牵连,散开的肋骨会在肌肉的牵引下自动外翻,呈现一种翻开的状态。于是商人管这种状态和这种祭祀方法叫做“卯”,卯这个字在甲骨文中的字形,也真实的反映了这种形象。
前几年有一部热播的美剧,名叫《维京传奇》,里面讲述里面讲述维京传奇海盗朗纳尔·洛德布罗克的儿子们为了给父亲报仇,曾经对英格兰的诺森布里亚国王除以一种异常残忍的“血鹰之刑”,方法也是将受刑者从背部打开,使其肋骨外翻,最终让其窒息而死。

这个形象是不是跟“卯”的甲骨文很像?
真实的历史上,中世纪的维京人似乎相信用这种刑罚处死俘虏可以讨好神明和自己的先祖。
而无独有偶,我国商代同样以人作为祭品的人牲当中,似乎同样流行这种做法,只不过它在商代人那里不叫什么“血鹰之刑”而被高度简化为了象形的“卯”字。
在方位上,卯代表正东,考古发现很多被施以卯刑的人牲刚好也是朝向正东被献祭的——这种献祭方法可能与维京人一样,来自一种古老而神秘的太阳崇拜。

也正是卯这个字为什么能从一种人牲的祭祀方式,逐渐被固化为指代祭祀时的一种方向,并最终成为天干中的一格的原因。

所以,看看卯这个字吧,从这个字眼的血腥历史当中,你就能理解为什么它在现代汉语中除了代表天干中的一格,再没有别的用法——周革商命之后,这种异常残酷的人牲方式被禁止、绝迹了,于是人们慢慢忘却了这个字背后的本义。于是它成为了一个死文字。
根据一些考古学家的推测,不仅“卯”,像“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甲乙丙丁”等等天干地支,在商代的祭祀当中可能都是有类似意义的。
在商代,这些文字的背后,可能有一部复杂的“祭祀学”——杀什么样的人牲需要朝向什么方位,怎么动手,可能是一种非常庞大而驳杂的学问。而通过献祭人牲以与鬼神沟通,在商人(尤其是王室贵族)的生活中可能是非常频繁而重要的。现代考古学已经考证出的商代人牲数量就在三万人以上,真实数量肯定远高于这个数字。

但这就引申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卯”这样的曾经十分流行的血腥人牲方式和与之相配套“献祭学”,能够成功的被我们忘得这么干净?
之后,到底发生了什么?让华夏这个曾经在古文明中最为“尚鬼”、信奉鬼神力量以至于要大量血腥献祭的族群,一变而成为了全世界最为世俗、“敬鬼神而远之”的民族?
毋庸讳言,世俗化的思考方式,甚至成为了之后中国人有别于世界其他族群最重要的特征。
是的,在卯这个字的黑历史被忘却的背后,藏着一段有意被模糊、忘却,却又至关重要的中华民族世俗化变革。
中国人是怎样从最“尚鬼”的民族,一变而成为最世俗的民族的?其中的关键,就在周灭商被刻意隐瞒的故事中。

考古的证据发现,我们的民族在刚刚进入文明时代的时候,与世界上大多数文明一样,本来也是喜欢搞祭祀讨好鬼神的。而且我们的祖先也相信祭祀的物品越贵重,神明和祖先就越高兴。那毋庸讳言,人总比牲畜要贵重一些,于是人牲和人殉的习俗就出现了。
在被猜想为史书上的夏代首都的二里头文化遗址当中,就存在有一定数量的人牲遗骸,而且非常有意思的是,这些人牲主要集中于城市的炼铜区域当中。
这一点乍看起来匪夷所思,因为在石器与铜器混用的远古时代,炼铜可是绝对的高科技产业,炼铜族群尤其热衷人牲献祭,相当于现如今一帮设计芯片或搞粒子对撞的工程师、科学家热衷于跳大神,这怎么可能呢?
可是如果你深入理解一下古人的思维方式就明白了——远古时代可没有科学思想,炼铜师们不知道炼铜的原理,他们只是按照被传授的经验,去碰运气、去赌这一次的矿石能不能炼出铜器,铜器的质量又怎样。

可是这种瞎蒙的冶炼方式,无法控制的变量太多,铜矿的质量、伴生矿的杂质干扰、炉火的温度等等等等。炼铜的工程师们不知道更无法控制这些变量,于是被变量折磨疯的他们就会本能的相信,也许冥冥中有鬼神决定了他们能否成功,于是他们本能的想去讨好这些鬼神。
这就像最近热播的《三体》网剧加的那段原创戏——当观测天文的沙瑞山无法解释更无法掌握“宇宙闪烁”时,他就开始搞各种类似迷信的“控制变量”,试图用无因果联系的主动行为,影响结果。

是的,由于无法把握自己的工作的结果,不知道自己的“农场主”是谁,人牲这种有着浓厚迷信感的习俗,反而在那个年代最“技术流”的炼铜族群当中最为兴盛。
而商代,很可能恰恰是商人的先祖联合这些炼铜族群建立的。于是商朝就呈现出两种看似矛盾的特质——
一方面它在当时的中原诸部族中是技术最领先的,可以用先进的青铜器对周边石器部落形成降维打击,碾压和兼并他们。

另一方面,商人却又是在鬼神之事上最迷信的,他们承袭了炼铜部族喜欢人牲的传统,并将其大幅扩展。从早商时期开始,商人就习惯于把自己的跨部落统治,也和鬼神的眷顾联系在一起。并认为只有通过不断奉献贵重的祭品——人牲的方式,继续讨好鬼神,自己的政权才能像铸铜的炉膛产出铜水一样,维持兴盛。
应当说,对于一个远古跨部族政权来说,这种“事鬼”是一种残忍却又聪明的统治方式,因为在青铜武器保障的武力之外,又给商王朝多增添了一层合法性背书——我能统治你们,是因为我依靠战争抓的俘虏足够多、献祭的人牲多、鬼神足够开心、于是眷顾我,继续支持我打胜仗,抓更多的俘虏来献祭鬼神。——这是一个逻辑自洽的循环论证,可以威慑其他部族不敢挑战商王朝的权威。
如果我们观察16世纪中美洲阿兹特克文明威慑周边城邦的历史,你会发现两者在统治手段上是出奇相似的。

可是时间的推移,一些变化一定会发生——
比如交流中,越来越多的周边部族开始学会使用青铜器,商王朝的技术碾压优势开始丧失。通过战争获得俘虏变得越来越难了。
同时,很多商人在与其他部族的交流当中意识到对方也是人,并接受了他们更加温和、不那么残忍的祭祀方式。
于是一场“宗教改革”就发生了——从商王仲丁开始,获得俘虏日渐困难、受到周边部族影响的商王终于开始尝试减少人牲的数量,改用其他的方式祭祀,但是这就造成了商朝守旧势力的恐慌。他们觉得,你们改革派这是搞“以夷变夏”啊,我们要抵制文化入侵啊,要始终坚持杀人事鬼的传统,一万年不动摇!于是改革派和保守派就斗了起来,商朝由此走向了中衰的乱局中,史称“九世之乱”。
而在九世之乱中,最终获胜的,很意外的是守旧派。这源于另一项技术传入中国所带来的蝴蝶效应——马车。

马车技术的传入,给原本已经被稀释的商朝青铜技术优势带来了新的活力。手持青铜戈的武士从此可以在战车上所向披靡。人牲的“供给端”问题被解决了,商朝重新在外战中大量获胜,守旧派将此归功于商人事鬼的传统,因此重新统一了部族思想。
公元前1320年,盘庚迁殷,商朝将首都设在了黄河北岸的殷(以及之后的朝歌)。这个位置的选取非常有意思,之前的历代商都,都是更靠近铜矿产区的黄河南岸,但盘庚却选择把都城建在了南方铜产区与北方太行山马产区的连线中间点上,这标度着商朝赖以立国的技术优势,从单一的青铜器,转向了青铜+马车。

与此同时,吸取“九世之乱”的教训,另一种新的“神学体系”也开始面目清晰了——商王开始在祭祀当中越来越多的把自己的祖先也当做“鬼”来祭祀,以强调商朝死去的历代先祖有某种超自然的威能,与昊天上帝等自然神不同,他们当然只会保佑自己的子孙万世坐稳王位,并且更倾向于保佑那些更像自己、更能贯彻自己传统(所谓“肖”)的子孙。
到了晚商最后两位王——帝乙和帝辛(纣王)时代,商朝已经直接开始称呼在世的国王为“帝”,而帝这个字之前只是用于称呼被祭祀、享受人牲的鬼神的。
很明显,商朝在搞了数百年统治实验之后,终于摸索出了神话自家君主世系这条思路。
是的,中国人特有的祖先崇拜,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出现了。

但这又产生了另一个问题——与固定数量的自然神明不同,祖先的数量是会随着王朝的代际传承不断累加的,每一个祖先都成了神,都需要讨好,按照商朝的祭祀传统,这就需要大量的人牲来进行祭祀。
于是到了晚商时代,人牲“供不应求”的危机在商王室淫祀犯懒的情况下再次出现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同时也遵循“越有价值的人牲,祭祀效果越好”的思路。商王室开始杀已经臣服的部族奴隶、平民、贵族,甚至是自己王室内部的贵族来进行祭祀。
传说中商纣王的残暴,他挖自己亲叔叔比干的心脏,以及把周文王的儿子伯邑考做成人肉酱等行为,其实都是商代淫祀走向疯狂与死局,临近崩溃时的一种表征。

商代这种结合技术优势和鬼神信仰的统御体系,在经历数百年的运转之后,冗余积累已经太大了,系统临近崩溃,亟待更新,所以才会出现这种乱纪元式的疯狂。
而这种乱纪元的终结者,最终还是出现了,他就是周文王。

非常讽刺的是,周文王率领的周族,最早其实就是替商王朝当“人牲贩子”起家的。周人原本是羌人的亲戚,但却当了二五仔,靠捕捉羌人给商朝当人牲获得了商王的封赏。晚商时期,随着商王朝祭祀人牲需求量的增加,周部落也越发崛起。最终,本属偏邦首领的周文王,获得了亲自去朝歌觐见,上贡人牲的资格。
可是自身没有人牲习俗的周文王,一到了朝歌,就被这座商都的繁华、糜烂与残酷吓坏了,他亲眼看到了自己上贡的人牲是怎样成批的被残忍杀死,又听说了纣王为了追求祭祀效果,开始杀部族首领甚至王室贵族的传说。
所谓“君子远庖厨”,原本自己就是人牲贩子起家的周文王自己也无法容忍了,他应该确实说了一些非议,然后被监视他的崇侯所举报,关进了羑里。羑里就是一座专门关押人牲,尤其是高级人牲的监狱,纣王这时候,应该也是起了那他祭天的心思——正好高阶人牲稀缺,你送上门来的,岂有不要之理?
但就在羑里等待被“卯”了的时候,周文王也开始了他的“龙场悟道”——“文王拘而演周易”,由于从土乡下来到了朝歌这样的大城市,又处于天天等待被祭天的焦虑当中。周文王对商朝的鬼神体系,“上帝”(昊天上帝)到底是否会喜欢人牲这种残忍的祭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他开始创新一种新的神学体系,以试图与上天沟通。这就是“易”。

易的意思,其实就是变。
文王的这套体系,其实是与商朝的神学思想相对提出,文王认为上天的旨意是在不断变化的,所谓“天命靡常”,所以人类不可能通过一种固定的方式(比如祭祀人牲)去讨好鬼神,人能做的只有顺应“易”的变化,去做相应的事情。
这就是后来周人行动的理论基础。周文王在神学理论上首先击碎了商朝的合法性基础——
你纣王总强调说你献祭了多少人牲、身份如何尊贵、所以鬼神会多么满意、因此眷顾你。嘿!我偏不认。我说天命这个东西就像天气一样是不断“易”、不断变化的。
而且“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尚书·泰誓》)老百姓是怎样评价你这个行为的,鬼神就怎样评价你这个行为!那么在我们这些周边部族普通人看来,你滥杀人牲就是一种残暴。
所以“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诗经·大雅·文王》),我现在就是受了天命,要对你殷商发动革命。

约公元前1046年,文王的儿子武王伐纣,牧野之战爆发,被周人率领的各部族联军打的“血流漂杵”的商纣王逃回朝歌,进行了商王朝最后也最为贵重的人牲祭献——他穿上宝玉衣,登台自焚而死。

也许商纣王是试图用这种真正原教旨主义的“自我牺牲”的方式对他仇恨的周人进行诅咒。而诡异的是,这次诅咒似乎成功了。在“革命”成功后第二年,周武王姬发就生病了,不久去世。但他死前把国政托付给了弟弟周公旦,而周公旦成为了那个真正完成这场变革的人。
他彻底推翻了之前商人“事鬼神”的传统,甚至不惜为此毁灭朝歌这座都城、开掘历代商王的坟墓、熔毁祭祀用的铜鼎,并删改之前一切的历史记录……
总之周公旦几乎堪称一位“清零者”,对商朝留下来的一切传统,除了象形文字本身,和被他认为有用的祖先崇拜被刻意保留,周公几乎让一切从头开始了。

而在新出发点上,他提出了一套系统“礼乐体系”。发扬了他父兄的主张。周公认为,人与神鬼之间,是有一条不可逾越的屏障的,人即便再尊贵,也只能做“天子”,而不能像商王所梦想的那样“飞上天与太阳肩并肩”,成为神明本身。所以“天命靡常”,又曰“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对统治者来说,祭祀给鬼神多么贵重的礼物(人牲)以试图讨好他们,也没有把天下治理好、让亲戚与百姓和睦富足,以说明自己就是个“有德之人”更能获得上天的眷顾。
这就是周公为华夏确立的新鬼神观、宗教观。数百年后,周公的一位铁粉将周公旦的这种态度高度总结为“敬鬼神而远之”,并高度称赞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是的,这位铁粉就是孔子。

对比起来,你会发现很有意思。周公的这种“神学改革”的方式,跟马克斯·韦伯笔下的“新教伦理”有很多异曲同工之处——他们都不否定神的存在,但否定了人可以通过某些祭献(无论人牲,还是赎罪券)直接去讨好神明,而认为人获得神明眷顾的凭证,需要在现实的成功中获得(有德,或者自证自己是“上帝的精兵”)。
所以如果说,新教改革所确立的新伦理开启了欧洲的世俗化时代。那么中国的世俗化时代,则是早在“周革商命”时就完成的。这一点上,我们实实在在地领先了西方两千多年,也就造成了中华民族为什么成为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最世俗化民族。
所以你看,中国人过年在老外看来也许就很奇怪。其他民族的过年,无论基督教文明也好、伊斯兰教文明也罢,甚至日本、印度等就在我们周边的文明,他们的年节都是有非常强烈的宗教文化参与的。要去教堂、寺庙或神社,祈祷神明的保佑。
宗教设施是世界大多数民族过年的主要场所。

唯独我们的过年,几乎不祭祀任何超自然的神明,也从不去教堂或者神社,乞求神明的眷顾、恩典。由于周公刻意保留甚至强化了晚商时代兴起的祖先崇拜,所以中国人过年时会祭一下祖,但相比于更世俗化的阖家团圆、吃饺子。这种准宗教仪式依然占了小头。
我们的年味里,全是浓浓的世俗化,宗教味儿是很少的。相比调节人和神鬼的关系,我们永远优先重视调节人和人,尤其是人和家人、亲戚的关系。
这都是三千年前的那场革命产生的蝴蝶效应。

而所谓矫枉过正,也许正是因为有了商代过分亲近鬼神的极端,经历周革殷命之后,我们的民族反而向着世俗化的另一个极端一去不回头。所以中华文明,在世俗化这一点上是非常早熟的。
当然的,正如早熟的孩子往往会有别的问题一样,中华文明在世俗化上的过度早熟也会造成很多弊端——但这方面,大过年的,又已经写了这么长,就不写了,有时间我们再慢慢说。
总之,从“卯年说卯”聊起,到商周革命,再聊回过年。我们从卯这个字的黑历史中,终于窥见了我们的一种文化基因在三千年前,究竟是怎样被塑造的。
透过一切血腥、疯狂、反思、变革与新生,我们终于成为了世俗的我们,而中国年也终于成为了世俗的中国年。
让我们回忆那段曾经被淡忘的故事,记起那句淫祀与狂乱中想起的呐喊——“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

既然谈到了易经,我就送给大家一份卦象,表达一下新年的祝福吧:
革卦

易经有云:“九五,大人虎变,未占有孚。上六,君子豹变,小人革面。”
性格即命运,而无论民族还是个人的性格,都不是不可变革的——三千年前,我们就曾做到过。
过去的一年,大家都不容易,新的一年,愿我们都有所变革。